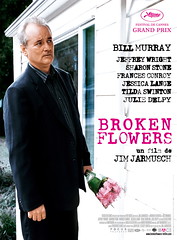我很愛吃蛋黃酥,尤其是郭元益。但是上飛機前,因為種種原因,所以只能在香港轉機時,買了兩盒榮華月餅湊數。
迷你蛋黃白蓮蓉酥和迷你皮蛋酥。
為什麼要加「迷你」兩字?大概是因為港式月餅都大得像半個喜餅,所以對我們來說正常期望值中的月餅大小,對香港人來說算迷你。
我就帶著兩盒月餅,行經曼谷、巴林,回到了巴黎。
室友對於這兩盒月餅非常狂喜,畢竟她來法國多年,只有二OO三年暑假回過一次台灣。像我這種半年回台灣一次的好命留學生,可以想像但難以真正體會她那種思鄉之情。
她堅持,月餅一定要撐到中秋節吃。所以在這個禮拜,我和室友只偷偷各吃了一個皮蛋酥,不過我們都覺得太甜了。
「中秋節有沒有什麼活動?」室友問。
「啥活動?烤肉啊?去公園吹冷風跟流浪漢一起烤肉還是在一樓過道烤肉讓鄰居和管理員罵?」我不是很認真地回答。
「烤肉是一定要的。」室友很惆悵。
後來我們折衷,決定去吃韓國烤肉。
昨晚,兩個女人在ODEON的街道來回走著,尋找她朋友介紹的一間韓國烤肉店,而我的包包裡還塞著兩盒月餅。
究竟是我們找錯巷弄還是禮拜天沒開並不重要,最後我們隨便進了一間意外好吃的墨西哥餐館,當然很應景各點了兩份BBQ。
「中秋節快樂!」室友拿她的COCA LIGHT敬我的海尼根。我覺得這個動作一出現,好像很淒涼。
這間墨西哥餐館的份量很多,吃到剩一堆食物,當然也沒有人有興致拿出月餅嗑。
接著去喝酒。
對我來說,喝酒才是適合節慶的活動啊!
那間叫做「AZ」的酒館,重拾我對法國調酒的信心,坐在吧台喝了一口長島冰茶,非常感動。
「這是我在法國喝過最好喝的調酒哪!」我努力平穩聲音不要太激動。
從諾曼地喝到巴黎喝到蒙比里埃喝到雷恩,這一年來我對法國的調酒給的評比是不及格,以致於我每每點了一杯調酒之後,立刻要再點啤酒沖淡味覺的折磨。
依據我的評比法則,一間酒館的長島冰茶好不好喝,可以定生死。
真好,總算讓我找到可以喝酒的好地方了。
因為是禮拜天晚上的關係,店裡人不多,大部分的客人都是明天不用上班上課的外國觀光客。
後面一桌澳洲來的女孩,愉悅地舞動肢體,很快就和另一桌的外國觀光客和樂融融。
有個心機很重的黑人,開始吹喇叭,出來喝酒帶啥樂器?

原本我靜靜坐在吧台喝酒,不一會兒就遭受池魚之殃,被那些瘋了的觀光客抓下去一起跳舞。
個人覺得自己對於舞蹈有嚴重的肢體障礙,所以只能很尷尬像壞掉的洋娃娃踏踏腳擺擺手。
愛跳舞的室友對著被團團圍住的我說:「妳很受他們歡迎耶!」
我好想哭!
接著我就趁亂拿著酒杯和煙躲到角落的沙發去,遠離是非之地。
那兩盒月餅,終究沒有在中秋夜亮相。

回家的路上,抬頭看天上的月亮,並沒有像我在去年夏天諾曼地看到的那樣「大到像臉盆」,小小的,也不很圓。
聽說農曆十六號的月亮其實比十五號圓,但我並沒有興趣今天晚上跑出去看月亮。
剛剛吃了顆蛋黃酥,覺得,還是太甜了。